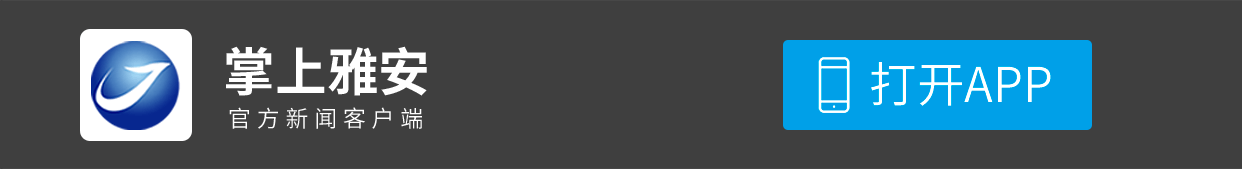高高的二郎山
高高的二郎山
□ 小霞
每每说到二郎山,总会想起父亲。
父亲10多岁时,被他当过红军的舅爷从安徽老家带到了四川。到四川后,父亲跟人学汽车驾驶。他虽然没读多少书,但是聪明好学,很快就学会了,并在康定汽车运输公司参加工作。康定汽车运输公司组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承担了甘孜州绝大部分老百姓出行和生产、生活物资的运输任务。
记忆中,父亲开过货车,后来因为技术好,又被安排开客车,汽车生涯持续了三十多年。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川藏线是连接川藏的唯一纽带。父亲每次从甘孜州跑车出来,险峻的二郎山是必经之路,也是父亲行车翻越最多的高山。那时候流传着一句顺口溜,“车过二郎山,犹闯鬼门关”,足以证明二郎山的险峻。
父亲跑车时,时常轮换带上我们三兄妹,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。翻越二郎山,十分考验驾驶技术,特别在积雪的冬天,更为艰险。从山底开车上山,由于道路狭窄,弯道众多,每次上山,对人和车都是艰巨的考验。父亲全神贯注,熟练地打着方向盘,车子轰轰隆隆地越过一道道弯路。有时道路结冰,父亲就下车挂上链条再走。每次车到山顶,放眼望去,盘山公路犹如一条盘伏的巨龙。下山也不能松懈,车速不能太快,刹不住车就危险了。天气好的时候,父亲偶尔会停下车来,带我们去摘点野花,或玩玩山边的瀑布流水,那清凉的感觉沁人心脾。
父亲出车如果是往甘孜州走,往往要跑上十天半月才能回家,遇上塌方堵车,时间会更长一些。路上饿了,就吃点母亲给他备的干粮充饥,经常跑到晚上才能吃上一口热饭。父亲基本把四川都跑遍了,跑得最多的还是甘孜州,还跑过几次西藏,货车里装有蔬菜、粮油、百货,还运过自行车,自行车可是当时“三转一响”里面的“一转”。那个时候,父亲还给家里买过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让在乡下供销社工作的母亲很有面子。
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,瘦高个,眉眼深邃,高高的鼻梁,走路总是挺直脊背,衣服总是洗得很干净。父亲和母亲相识于雅安,那时母亲只有十七八岁,梳两条辫子,面容清秀。和母亲结婚后,父亲就在雅安安家了。
母亲是家中老大,下面还有八个年幼的妹妹。外公因为年轻时经商做过生意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曾被关“牛棚”。没有了收入来源,一家老小过得十分艰难,连吃饱饭都是奢望。父亲除了养育我们三兄妹外,还承担起照顾外公一大家的责任。
印象中,父亲冬天经常穿着一件棉大衣。开车时,父亲嫌棉大衣笨重,时常把棉衣脱下来只穿着线衣开车。那时,驾驶员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,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生计。因为要时常接济母亲娘家人,也只能算勉强维持生活,但父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
在家时父亲言语不太多,高兴时会用他那被“川化”的安徽方言给我们哼两句家乡小调。
父亲有四兄妹,他排行老二。在雅安安家后,因为忙于生计,且路途遥远,父亲只回过几次安徽老家,但总会定期给远在老家的奶奶寄钱回去,奶奶也来过几次雅安。
常年跑车,父亲和大多数驾驶员一样,喜欢抽烟喝茶,烟抽多了,肺总会有些毛病,只要父亲一咳嗽,母亲就说“老头子,少抽点烟嘛”。但是过几天又一条一条地给父亲买烟。母亲常说,你们爸爸一个人在雅安不容易,他喜欢吃什么就尽量买,反正都这把年纪了,不需要戒烟了。1987年,我考上师范学院,家里每月给我寄50元钱,那是家里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。供我读书那几年,父亲抽的都是最便宜的烟,这是母亲后来给我说的。
二郎山隧道通车后,我们三兄妹专门开车带父亲和母亲去看二郎山隧道,隧道长四千多米,开车短短几分钟就从山这面到达山那面。父亲十分激动,“简直太了不起了!想当年我们翻山要走一整天哦!”又说起早早离去的同事,父亲红了眼睛。
2018年,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,享年79岁。父亲走后的第四个年头,母亲也因病离开了我们。
回望过去,追忆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光,一切都历历在目,仿佛还在昨天,是那么温暖,那么真实。作为儿女的我们,也早已为人父母,想到远在天堂的父母,心总会疼痛,不惑之年才深切地体会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: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如今,时代变迁,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生活条件大大改善,贫寒饥饿已成为过去。高原风光依旧,但父辈们付出的青春、挥洒的汗水,是我们永恒的记忆。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总会想起父亲那瘦高挺拔的身姿、奔波劳碌的身影,是那么伟岸、坚毅,正如那高高的二郎山。
编辑:高菲菲
审稿:程普 唐砚玉


 分享到
分享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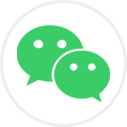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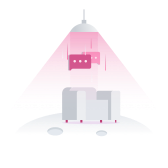 还没有人发言,快来抢沙发吧
还没有人发言,快来抢沙发吧